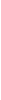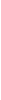谁要拯救心机美弱受(弯掰直) - 36.落差
冰冷、潮湿、剧痛。
意识像是沉在深海的碎片,偶尔被翻滚的浪头推到边缘,窥见一线天光,随即又被拖入更深的黑暗与混沌。
凌烁知道自己病了,而且病得很重。
从被海水冲上岸滩,湿透的衣服紧贴着皮肤,被初冬凛冽的海风一吹,寒意便如同附骨之疽,瞬间钻进骨髓。
本就因绑架、跳海、凫水而耗尽的体力,在持续的寒冷和高烧面前,迅速溃不成军。
他蜷缩在粗糙的沙砾上,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,牙齿咯咯作响。
额头上烫得惊人,眼前却阵阵发黑,耳边只有自己粗重滚烫的呼吸和远处单调的海浪声。
喉咙干渴得像要烧起来,每一次吞咽都带来撕裂般的疼痛。
他隐约感觉到有人在拖拽他。
力道不大,甚至有些踉跄,却带着一种固执的、不肯放弃的劲儿。
是白薇。
白薇自己也狼狈到了极点。
单薄的针织裙和大衣吸饱了海水,沉重冰冷地贴在身上,勾勒出她微微隆起却尚不明显的小腹轮廓。
长发湿漉漉地贴在苍白的脸颊和脖颈上,嘴唇冻得发紫。
每走一步,都像踩在棉花上,冰冷和虚脱感阵阵袭来。
但她不能停下来。
这片海滩空旷荒凉,举目望去,只有嶙峋的礁石和远处稀疏低矮的植被,不见人烟。
天色越来越暗,海风越来越冷,如果找不到遮蔽和帮助,她和凌烁很可能会死在这里。
尤其是已经快要不行的凌烁。
她怕。
怕这陌生的环境,怕无边无际的黑暗和寒冷,怕腹中孩子可能受到的伤害。
但更让她害怕的,是凌烁会死。
这个念头让她自己都感到一阵扭曲的荒谬。
她不是恨他入骨吗?不是刚刚才拉着他跳海,想要同归于尽吗?为什么现在却怕他死掉?
原因复杂得让她心头发堵。
其一,也是最现实的,她对这里一无所知。
凌烁虽然可恨,但至少是个活人,是个曾在危急关头与她一同挣扎求生、甚至在海里拉了她一把的人。
如果他死了,她就真的只剩下自己一个人,面对这无边无际的未知和恐惧。
那份孤独和绝望,光是想想就让她战栗。
其二,她不允许。
凌烁怎么能这么轻易地死掉?
他毁了她的清白、名誉,让她陷入如此不堪的境地,还连累她被绑架、跳海,差点葬身鱼腹!他欠她的还没还清!他还没有付出应有的代价!他怎么可以就这么简简单单地病死、冻死在这个荒凉的海滩上?那太便宜他了!
其三,抛开那些怨恨不提,就在几个小时前,在冰冷刺骨的海水里,是他抓住了她挣扎的手臂,带着她朝着海岸拼命游。
尽管她知道那可能只是出于求生本能或别的算计,但那份支撑是真实的。
她白薇再恨,也无法对刚刚救了自己的人,立刻做到见死不救。
还有更隐秘、更让她不愿深究的原因……
她想到顾宸。
如果凌烁死了,顾宸会怎么想?
那张照片的秘密,楼梯间的真相,还有……这个可能存在的孩子……许多事情会随着凌烁的死亡变成永久的谜团,或者,以更糟糕的方式爆发。
她不敢赌。
她也曾闪过更黑暗的念头。
比如,趁他病重,将他丢在这里,独自去寻找生路。
甚至……让他“自然”死亡。
这样,很多麻烦似乎就一了百了了。
但当她低头,看到凌烁紧闭双眼、眉头紧锁、因高烧而泛起不正常潮红的脆弱侧脸,那些念头就像遇到阳光的冰雪,迅速消融了。
不是因为心软,而是因为一种更深层次的恐惧——对彻底堕入黑暗、背负一条人命的恐惧,以及对顾宸知晓后可能反应的恐惧。
最终,她还是咬紧牙关,用尽最后一丝力气,将凌烁一条胳膊架在自己肩上,半拖半抱,深一脚浅一脚地,朝着远处那点隐约的灯火方向挪去。
每一步都沉重无比,凌烁几乎全部的重量都压在她身上,冰冷的湿衣摩擦着皮肤,带来刺骨的寒意和摩擦的痛楚。
不知走了多久,就在白薇觉得自己也快要撑不住倒下时,他们终于靠近了那点灯火。
那是一个极其简陋、低矮的石头房子,窗户透出昏黄微弱的光。
屋外堆着渔网和破损的木桶,空气里弥漫着海腥味和柴火烟味。
白薇用尽力气拍打着粗糙的木门。
门开了,一个满脸皱纹、皮肤黝黑、穿着破旧棉袄的老爷爷探出头来,看到他们这副落汤鸡般狼狈不堪的样子,浑浊的眼睛里满是惊讶。
白薇急忙想说明情况,寻求帮助。
可她一张口,才发现自己的声音嘶哑得厉害,而且她说的话,老爷爷显然一个字也听不懂。
老爷爷说了几句什么,语调奇怪,发音拗口,是白薇从未听过的方言。
沟通的障碍让白薇瞬间感到了更深的绝望。
她只能拼命地比划,指指昏迷不醒、浑身滚烫的凌烁,又指指自己湿透的衣服,做出寒冷和需要帮助的手势。
焦急和无力感让她眼眶发热。
老爷爷皱着眉头看了他们一会儿,又抬头看了看阴沉的天色和远处黑暗的海面,最终,还是侧身让开了门,示意他们进去。
屋子很小,很简陋。
地上是夯实的泥土地面,墙壁是粗糙的石块垒成,唯一的家具就是一张破旧的木桌、两把凳子和角落里的土炕。
土炕上铺着干草和破旧的被褥。
屋里生着一个小小的炭盆,散发着微弱的热量,却已经是此刻无上的温暖。
老爷爷帮忙将凌烁扶到炕上。
白薇顾不上自己,连忙去摸凌烁的额头,烫得吓人。
她焦急地看向老爷爷,比划着“水”、“药”的动作。
老爷爷似乎明白了,转身去灶台边,用粗陶碗盛了一碗温水过来,又从一个脏兮兮的布包里摸索出几片晒干的、不知名的草药叶子,示意白薇给凌烁喂下。
白薇看着那几片来历不明的干叶子,心里直打鼓。
但她别无选择。
她费力地扶起凌烁,让他靠在自己怀里,一点点将温水喂进他干裂的嘴唇。
凌烁在昏迷中本能地吞咽了几口。
至于草药,白薇犹豫了一下,还是掰下一小点,混在水里让他喝了。
死马当活马医吧。
老爷爷又找来两套虽然破旧但还算干净的粗布衣服,指了指旁边一个用草帘隔开的小小空间,示意白薇去换下湿衣服。
白薇谢过(尽管对方可能听不懂),拿着衣服走到帘子后。
脱下冰冷湿重的衣物时,她忍不住打了个寒颤,皮肤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
换上粗糙的、带着皂角味的粗布衣服,虽然不合身,但干燥的感觉让她稍微好受了些。
她摸了摸自己依旧平坦的小腹,心中稍安。
她走出来,看到老爷爷已经将凌烁的湿衣服也扒了下来,给他换上了另一套男式粗布衣,并盖上了那床散发着霉味和阳光混合气味的破被子。
做完这些,老爷爷指了指炕,又指了指白薇,意思很明显——地方小,只有这一张炕,你们凑合吧。
然后他佝偻着背,走到炭盆边坐下,不再理会他们。
白薇看着那张窄小的土炕,和炕上昏迷不醒的凌烁,心中五味杂陈。
她从小到大,何曾受过这样的苦?何曾住过这样破败的地方?何曾需要与人挤在一张炕上?
巨大的落差感让她鼻子发酸,但环顾这简陋却给了他们遮蔽和一丝温暖的石头房子,看着老爷爷沉默的背影,那份感激又是真切切切的。
至少,他们暂时活下来了。
就在她感到无助和茫然时,木门又被推开了。
一个穿着同样朴素、扎着两条麻花辫、脸蛋被海风吹得红扑扑的少女走了进来,手里拎着一个小鱼篓。
看到屋里的情景,她吓了一跳。
“阿公,他们是?”少女说的是略带口音的普通话,白薇勉强能听懂!
白薇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,急忙上前,用尽量简洁的语言说明了情况。
隐去了绑架等细节,只说是船难落水,同伴病重。
少女听得似懂非懂,但看着凌烁昏迷不醒的样子和白薇焦急的神情,还是点了点头。
“我叫桑桑。”少女的声音清脆,带着渔家姑娘的爽利,“这是我阿公。他不太会说官话。你们……先住下吧。阿公采的草药治风寒很管用的。”她看上去比白薇还要小三四岁,眼神清澈,透着善良。
有了能沟通的人,白薇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了一丝。
她连忙道谢。
桑桑看了看炕上的凌烁,又看了看白薇苍白的脸色,转身去灶台边忙活起来。
不一会儿,她端来两碗热气腾腾的、稀薄的鱼粥,里面只有零星几点鱼肉和野菜。
“家里……没什么好东西,将就吃点,暖暖身子。”桑桑有些不好意思。
白薇接过粗糙的陶碗,看着碗里清汤寡水的粥,再对比往日自己锦衣玉食的生活,心中又是一阵酸涩。
但她知道,这已经是这户贫苦人家能拿出的最好的招待了。
她低声道了谢,强迫自己喝了下去。
温热的粥水下肚,总算驱散了一些寒意。
夜里,海风呼啸着穿过石缝,发出呜咽般的声响。
炭盆里的火早已熄灭,屋里冷得像冰窖。
白薇和衣躺在土炕的外侧,凌烁躺在她内侧。
炕很窄,两人几乎挨在一起。
凌烁依旧昏睡着,但身体却因为高烧而持续散发着惊人的热度,在这冰冷的屋子里,竟成了唯一的热源。
白薇冻得浑身发抖,牙齿打颤。
起初她还尽量离凌烁远一点,但寒冷实在难熬。
睡梦中,她无意识地朝着热源靠近,最终侧过身,背脊轻轻贴上了凌烁滚烫的胳膊。
那热度透过粗糙的布料传递过来,驱散了她一部分寒意,带来一种生理上的舒适感。
她迷迷糊糊地,又往热源处缩了缩。
凌烁在昏沉中似乎也感觉到了什么,无意识地动了动,手臂微微收拢,竟将贴近的白薇半圈在了怀里。
白薇在睡梦中蹙了蹙眉,却没有挣脱。
极度的疲惫、寒冷,以及对这陌生环境潜意识的恐惧,让她在这病弱的、仇人的怀里,找到了一丝短暂而扭曲的安稳。
这一夜,在破败渔村的石屋里,在寒冷与高热的交织中,两个本该势同水火的人,因着生存的本能和极端的境遇,暂时依偎在了一起。
而窗外,是无边无际的黑暗大海,和未知的明天。
添加书签
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/提交/前进键的